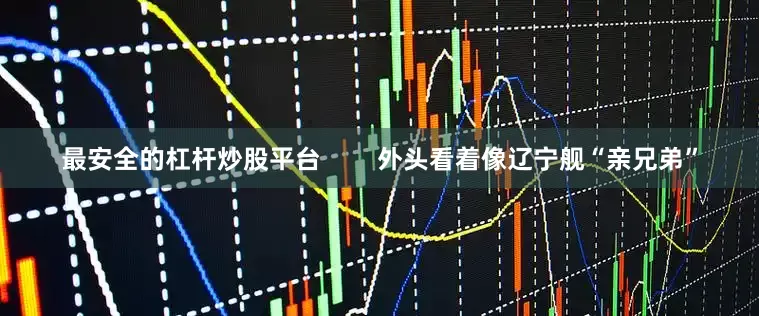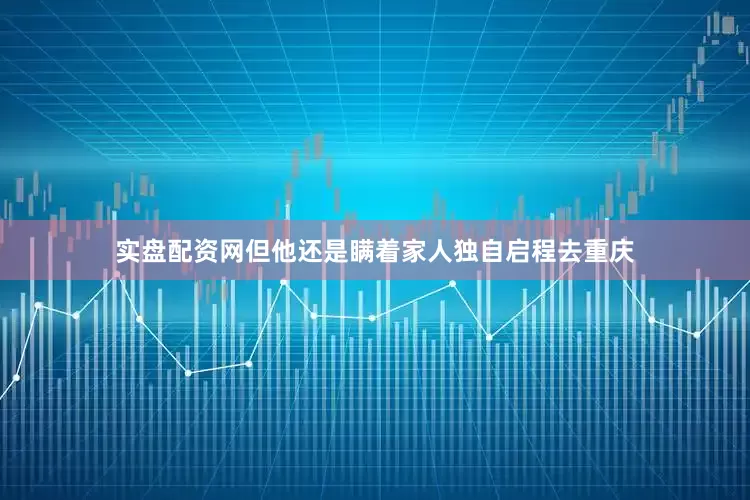
1989年,离开故乡整整48年的台湾老兵曲光镛,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,终于踏上了返回山东青岛老家的路途。此时已经67岁的他,身着一套时尚的西装,精神饱满,仪表堂堂,仿佛时间在他身上没有留下太多痕迹。
其实,如果不是弟弟一次次热情地邀请,甚至主动提出承担他的路费,还承诺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他,曲光镛本不打算回家。他内心深处感到羞愧,怕面对那些多年未见的亲人。但面对弟弟的盛情款待,他实在无法拒绝,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回去。
随着回乡的日子渐渐临近,曲光镛的心情却愈发复杂。这种复杂中既有“近乡情更怯”的紧张与焦虑,也夹杂着深深的愧疚感。他不知该如何面对那个被他离弃了整整48年的发妻,心里满是纠结与不安。
曲光镛反复思考,最终还是按照弟弟提供的地址,走到一处熟悉的老房子前。尽管他知道屋内住着家人,但站在门前的他却迟迟不敢敲门,似乎被无数回忆困住,久久不能行动。
童年的记忆,亲人的叮咛仿佛就在耳边回响。尤其是当他听见那熟悉的胶东方言声声入耳时,心头更是涌起一股暖流,提醒他自己终于回到了家乡……
“你……你是谁啊?”正当曲光镛沉浸在回忆与激动中时,门忽然打开了。一个准备出门买菜的老妇人走了出来。她看到门口这位满脸泪痕的老人,既好奇又惊讶,便问道。
展开剩余89%“我……我来找我的家人……我已经好多年没回来过了!”曲光镛哽咽着答道。眼前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让他感到似曾相识,但一时又想不起具体在哪里见过。
“你找的人叫什么名字?我对附近的人家都很熟悉,可以帮你指路。”老妇人热情地回应。
曲光镛没有立刻回答,掏出弟弟寄来的信,仔细对照上面的地址。确认这正是弟弟的家后,他又仔细打量起这位老妇人。
老妇人的脸上布满岁月的皱纹,略显驼背,但随着目光落到她那双小巧的小脚上,曲光镛内心的记忆终于被唤醒。
忍不住泪如雨下,曲光镛颤声说:“大姐,是我,我是光镛!”老妇人激动万分,尽管三年前已知道丈夫还活着,却没料到能亲眼见到他。她颤抖着手抚摸着曲光镛的脸:
“我苦等了你四十多年,等得心都碎了,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……”
事实上,曲光镛离家48年,妻子的容貌早已模糊,更何况时光荏苒,她已变化巨大。曲光镛能认出她,除了依靠弟弟给的地址,更重要的是认出了她那双一直劳作不停的小脚。
“你怎么这么傻呢?你怎么这么傻呢?”看着泪眼婆娑的妻子,曲光镛一把将她紧紧拥入怀中,嘴里喃喃自语,往昔的点点滴滴一幕幕涌上心头……
1922年,曲光镛出生于山东荣成。他有一个弟弟,父母自他小时候起便在青岛经商,自己则在爷爷的照料下成长。
父母经商有方,生意越做越大,逐渐在青岛站稳脚跟。家境优越,让曲光镛作为长子长孙,从小衣食无忧,享受最好的生活。
到了适龄读书时,他被送往威海求学。家人对他寄予厚望,尤其是爷爷视他为掌上明珠,期望他将来能成才继承家业,光宗耀祖。
对爷爷而言,传宗接代同样重要。曲光镛16岁那年,爷爷突然召他回家,安排他与比他大三岁的山东高密女孩成婚。
因此,两人结婚前根本未曾见面。用曲光镛自己的话说,他是糊里糊涂地与妻子结了婚。因妻子比他年长,他亲切称她为“大姐”。
曲光镛记忆中的妻子勤劳能干,婚后不久便承担起照顾爷爷和弟弟的重任,让他无后顾之忧。婚后不久,他又回到威海继续学业。
接下来的三年里,夫妻二人聚少离多。曲光镛志向远大,梦想有所作为;妻子虽文化不多,却一直默默支持他,任劳任怨,无怨无悔。
1941年,19岁的曲光镛毕业于威海一所中学,回到荣成老家任教。他和妻子婚后终于开始了朝夕相处的生活。
妻子非常包容他,任何重活家务都不让他沾手,常说他是文化人,不能做粗重体力活。
在曲光镛记忆中,妻子始终勤劳,但他对爱情一知半解,夫妻间鲜少深谈。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妻子那双灵巧的小脚,虽然娇小,却异常灵活。
然而,这种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。曲光镛内心躁动,不甘心终身窝在小地方教书,也不愿帮父母打理生意,他想投笔从戎,为国效力。
几个月后,听闻军校招生,他当机立断决定报名,虽知爷爷会反对,妻子也可能不赞成,但他还是瞒着家人独自启程去重庆。
临行前,他淡淡告诉妻子要去参加同学聚会,可能晚些回家。妻子未起疑心,只叮嘱他注意安全,目送他离开,却不知这别离竟成了四十八年之久。
曲光镛自己也没料到会走这么长时间。他原本计划战争结束后即归乡,平静生活,但命运并未如此安排。
离家两个月后,他考入军校,毕业后随部队奔赴前线。期间多次给家人写信报平安,但信件始终杳无音信。
抗战胜利的1945年,他申请退伍,计划回家团聚,回归教书生活。军旅生涯的苦难让他更珍惜平凡幸福。
但退伍申请未获批准,反被命令换防,辗转驻守杭州、上海。1949年,他被迫随部队乘船抵达台湾。
在台湾,他被派训练新兵,这些新兵多是被强征的壮丁,大家都极度怀念故乡,军营充满沉重气氛,深夜时常传出哭泣声。
曲光镛也极度思乡,后悔当年无声离去。他无法想象爷爷听闻他离家消息时的心情……
三年后,他再次递交退伍申请,幸运获批,但离开军营后感到更加孤独无助,身边无亲无友。
带着积蓄,他试图开设小工厂维生,却因缺乏经商经验,加上台湾经济萧条,工厂几经波折最终失败,只得转手。
之后,他过上闲散生活,但心中难安,决定开一家山东饭馆,既谋生计,也为与老乡老战友相聚提供场所。
饭馆开业后,老兵们纷纷光顾,曲光镛豪爽好客,常亲自下厨,陪酒至深夜,大家一边饮酒一边倾诉对故乡的思念。
渐渐地,这家饭馆成了老兵们的聚集地。曲光镛只收成本,有时还亏本,积蓄也几乎花光。长期喝酒让他染上酒瘾,身体每况愈下。
有人劝他成家立室,以后老了有人照料,但他总是拒绝,自嘲自己穷光蛋又有酒瘾,没人会看上他。
实际上,他还有另一个心结——对妻子的愧疚。虽然他以为妻子早已改嫁,但始终没勇气再婚。
1986年,许多台湾老兵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上了故乡亲人,朋友们也劝他给家里写信试试。起初,他忐忑不安,害怕收到消息,也害怕收不到。
在老部下的鼓励下,终于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家乡。
几个月后,一位老战友辗转多地归乡探亲,深夜悄悄将一封家乡的信交到他手中。
曲光镛焦急拆开,信是弟弟写的,告知爷爷和父母已过世,嫂子仍守着家门未改嫁,现与弟弟一家同住,盼他尽快回家。
信读罢,曲光镛久久不能平静,泪流满面,心中充满愧疚,觉得对不起家人,更对不起等待他四十多年的妻子……
此后,他频繁与弟弟通信,渐渐了解到家中变故,更感内疚沉重。
曲光镛离家后,妻子日日以泪洗面,四处打听他的消息,但徒劳无功。
邻居们的闲言碎语渐渐传开,说他携外人离家,不顾妻子,嘲讽她无能守夫。
妻子面对冷言冷语并无怨恨,甚至劝阻娘家人不要为难曲家,仍承担起照顾爷爷和弟弟的重任。
几年后,爷爷病重,临终时仍念着曲光镛的名字,并劝妻子放下执念,找个好人嫁了,说曲家亏待了她。
但妻子依旧拒绝改嫁。料理完爷爷后事,她前往青岛投奔父亲,开始尽心孝敬公婆。
后来,弟弟和弟媳生了孩子,夫妻俩忙于工作,妻子不仅照顾一家老小,还接送侄子侄女上学。
曲家人都非常满意她,弟弟和弟媳尊重她,教育孩子孝敬这位大娘。
又过些年,父亲临终前劝她别等曲光镛了,要重新开始,找个人相伴。
妻子哭着坚决拒绝:“爸,我是曲家人,生死都属于这个家。改嫁了,他回来就真没家了……”
弟弟弟媳生活拮据,妻子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,悄悄回了娘家高密。
小侄子得知后,骑车一百多公里去接她,但她仍不愿回青岛,怕成负担。
她将自己攒下的钱交给侄子,嘱咐他好好读书,随后让他回到青岛。
此后,妻子住在娘家老屋,开荒种地,收获时把瓜果送给弟弟一家,尽力帮扶亲人。
弟弟弟媳常来看望她,劝她回青岛,她始终拒绝。直到弟媳病逝,侄子侄女长大成家,她才回青岛照顾第三代。
曲光镛得知妻子多年为家付出,感动落泪,开始戒酒,攒钱想为家人做贡献。
年事已高
发布于:天津市配资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